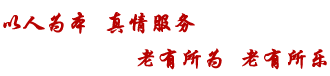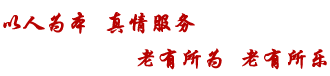作者简介
范绎,1944年12月出生,1966年7月参加工作,2004年12月退休,原经济学院教授,退休后,热爱绘画和摄影。
所谓双乐,其实是我的两个爱好。一曰画画儿之乐,二曰拍景儿之乐。
画画儿是我从小的爱好,得益于五、六十年代北京的中小学教育。那时的小孩儿每天下午放学做完不多的作业后,便可尽情地玩儿了。学校每周都有课外兴趣小组活动,我在高小、初中和高中一直都参加美术组,同时周末和假期还去西城区“少年之家”学画画儿。当然,课外活动都是自愿参加的。
回想起来,学画画儿最难也最枯燥的是画石膏像了,但这个环节不能免。石膏像很贵,我们只能在学校练习画它。相比之下,画静物、人像(包括自画像)和速写(课间画同学、上课偷画老师)就随意和有趣多了。直到上高中,我才得到一尊亚历山大分面石膏像,就是将人脸分成若干小立面的那种,难画且价钱贵,至今还收藏着。每每见斯,总会想起画他之艰难和尴尬:每周老师讲评时,若是交不出像样的习作,那才真是“压力山大”呢!
最快乐的记忆是老师带我们去写生。我们曾画过北海、胡同儿、阜城门和城外的农田草垛等,连玩儿带画可高兴了。再就是到处看画展了。像齐白石、徐悲鸿等大画家的画,不管懂不懂,看的可都是真迹呢!此外,还结伴溜进中央美院(当时座落于王府井)的展室,看人家出国临摹的某流派的油画,怪异的令我目瞪口呆。还胡乱闯进学生画室,看人家用泥巴雕塑头像,真是羡慕不已啊。一次听老师讲“清明上河图”是何等了得,我就独自跑去故宫细细地看了一遍(不知是否真迹)。忘了是在哪儿,看到了华君武的漫画展,乐不可支,回来给同学讲了老半天呢……在这七、八年的时间里,我在老师的教导下,在京城的文化氛围熏陶中,不知不觉地打下了绘画基础并提高了欣赏水平,且受益终生。
上大学和在工作岗位,这一爱好体现在画黑版报上。文革中还画过宣传画和漫画。由于当时常写大标语和抄语录,我又额外学会了写美术字。上班之余技痒,画过两本小人儿书,文革后竟得以出版了。而后的几十年,由于工作家务两繁忙,就很少动画笔了。但忙里偷闲,还是在鹅卵石上画过小画儿,涂上清漆摆在书桌上当“镇纸”;在白背心上画过卡通,送给学生、亲朋和孩子穿着招摇;也给出版商画过教材的插图。唯一与我专业沾点边儿的,是给《中国商业年鉴》画过彩色的统计图。
小时候我没学过国画,退休后正好看着书自学,每天也就有事做了。比如画工笔紫牡丹花,要求九染花头,即在熟宣纸上一遍遍涂色之后,花儿就会呈现出丝绒般的效果,而纸虽湿过多次,背面却毫不漏色。我惊叹和感恩祖先留给我们这独一无二的画纸和这神奇的绘画技艺!再如在生宣纸上画叶片,墨、色、水和手感相交融,只能一笔出效果,坏了不能改。我必须在几千遍的练习中,寻找最佳融合点。就这样不厌其烦地练下来,面对成品,一但自我感觉良好时,我整个人也就真的能乐在其中了。
用相机拍景儿则纯属偶然。孩子是摄影爱好者,技艺到了某一高段,相机就得升级,我便捡了剩儿。原本只想用其微距功能拍些花朵,留作画画儿时参考,不想却从端不稳相机开始,走到入了迷。也才发现,在这机器的“眼”里,自然风景远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要美若干倍。也没想到,从小时候第一次看欧洲印象派的画作,至今几十年已过,我才刚有点儿明白了:在相机里,逆光看风景,与莫奈画出的那些耀眼的风景画竟然一般无二;在相机里,夜空变幻多端,与凡高笔下的奇异星空何其相似乃尔。我惊叹这机器发明者的了不起,更仰慕百年前这些伟大画家的非凡眼光和艺术表现力。
拍景儿是一个发现美的过程。比如4月初,早樱花盛开及树梢时,赶上天空晴朗,站在树下抬头望去,花和兰天就会匹配成不同的美丽画面,再有合适的光加进来,画面即现清新之美。4月中下旬,晚樱花怒放压枝头时,赶上前一天下过点小雨,清晨天空晴朗,在逆光略带水雾中可拍出镶着金边的花朵,背后衬着多层的彩色光晕,画面即现朦胧之美。还有京城的皇家古建,真是令人屡拍不爽。比如北海的白塔,你略加注意就会发现,它在兰天之前、白雪之中、雨后白云之下,不断地变幻着自己,给人们呈现出它与天空的和谐之美。也可以去拍一段京城独有的高大的红墙,配上远处走来的小人儿,那可能是全世界的独到之美。若赶上春分、秋分节气,傍晚太阳在天上挂得久些,就可以在西城的胡同里拍夕阳,要是恰巧有鸽群飞过,那也许就是惟京城之美了……总之,我虽然上了年纪,拍技也不怎麽样,但我热爱生活,更热爱老家北京,所以对她百拍不厌。为了赶景儿、赶点儿、赶好天儿,人就不能懒,从而逼着自己早起、走出去,客观上也就锻炼了身体、愉悦了心情。每每拍了美景回来,一定要挑些做成视频文件配上音乐,上网发给亲朋、同学和同事去显摆(不怕丢脸),其实想法很单纯:就是不愿辜负了大自然的造化,想跟大伙儿分享美景,共同幸福快乐每一天。